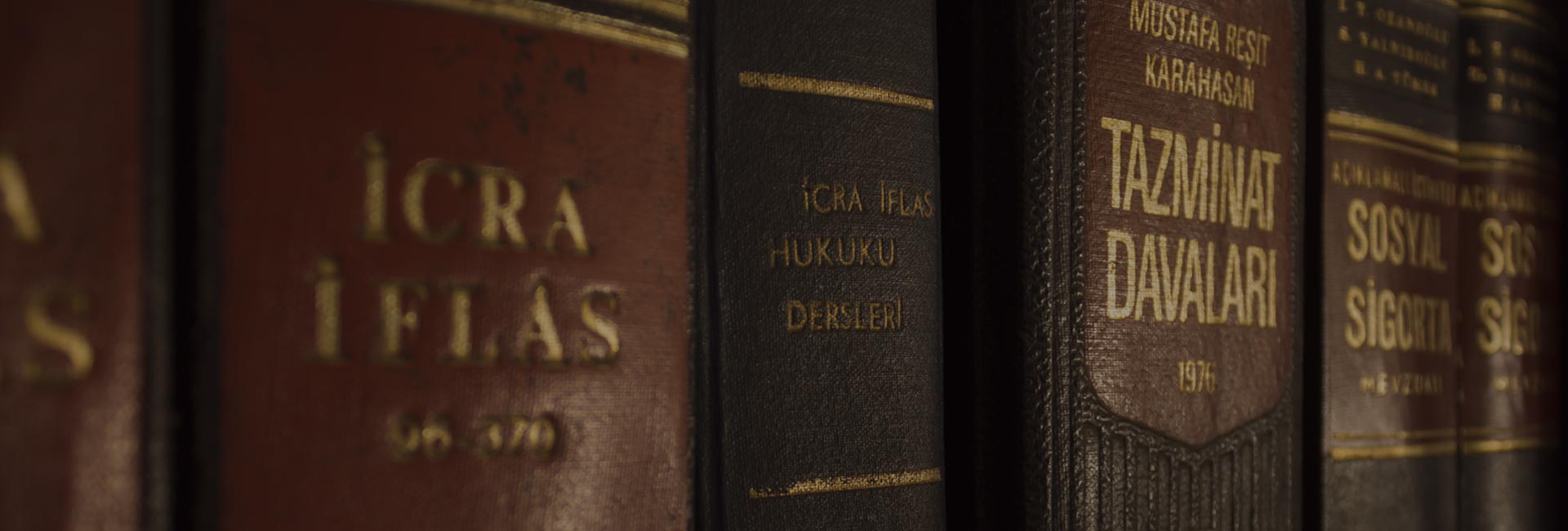出版
『商標法第十五条「代理人」の概念に対する法理的解析--「头包西灵」商標評審行政訴訟案の法の適用を兼ねて評論する』
時間:2018-06-29 ソース:2009-07-15
作者:蒋 洪義
一、 引言
我国现行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或禁止使用。”
根据原国家工商管理局局长王众孚2000年12月22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现行商标法的上述规定渊源于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相关内容——“如果本联盟一个国家的商标所有人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该所有人授权而以自己的名义向本联盟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国家申请该商标的注册,该所有人有权反对所申请的注册或要求取消注册,或者,如该国法律允许,该所有人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给自己,除非该代理人或代表人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
由此可知,我国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代理人”的涵义与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的涵义是一致的。由于巴黎公约和我国商标法均未对其中所规定的“代理人”的涵义和范围专门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当前的商标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上述“代理人”概念的涵义及其范围产生了较大的争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代理人”是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代理制度以及合同法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其涵义是指接受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相应的法律行为且由被代理人承受该行为之法律后果的人。在商标领域中,符合上述涵义的代理人主要是指商标代理人,即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的委托而代理其办理相关商标事宜的专业人士。因此,我国知识产权界包括商标行政执法部门一直都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来理解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以及我国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代理人”的涵义,进而认定其本义就是指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代理人。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一书,就将商标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解释为:“根据本条规定,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接受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委托进行商标注册,应当以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名义进行。如果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未经授权而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有权提出异议,对提出异议的商标,商标主管部门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对于已经注册的商标,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还可以根据本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自该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要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根据上述解释,该条款中所规定的“代理人”显然是被认定为商标注册代理人。
但是,从近年来所发生的涉及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情形的商标抢注争议案件来看,涉案的代理人基本上都是基于商事业务往来而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相反,商标注册代理人违反代理合同的约定而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的情形反而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若对上述规定中的“代理人”范围界定过于狭窄,局限于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代理人,则客观上将会导致该项法律规定形同虚设,无法实现其制止代理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注在业务关系中所知悉的被代理人商标这一立法宗旨。鉴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和商标局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商标审理标准》时,在广泛征求各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于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代理人”概念,在仍然坚持其本来涵义是指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规定的代理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办案实践,对其涵义和范围作出了一种广义的延伸,明确规定“该条所述的代理人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规定的代理人,也包括基于商事业务往来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也就是说,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实践中对商标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代理人”的涵义进行了扩大解释,将其扩大到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代理人之规定的经销商身上。
然而,这种扩大解释在知识产权界包括实务部门间引起了较大的争议。2006年4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针对“头包西灵”商标评审行政诉讼案作出(2006)高行终字第93号行政判决,首次用司法判决的形式否决了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其《商标审理标准》中所作出的上述扩大解释。该终审判决重新对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的涵义进行了判例阐述,指出“该条款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即指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代理其委托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请求查处侵权案件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人”。根据上述阐释观点,北京高院对于该条款中“代理人”的涵义,实际上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代理制度的规定并结合商标领域的实际情况,将其限定为商标代理人。
这样,在当前的商标行政执法实践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的理解就出现了两种近乎对立的观点。尽管北京高院作出的上述判决属于已生效的终审判决,但经有关当事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已于近日作出再审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该案。因此,对于商标法第十五条中的“代理人”涵义应当如何理解的争论,尚未最终见分晓。
笔者认为,在上述两种观点之中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符合巴黎公约的立法本意并应在今后的商标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得到统一的贯彻执行?抑或在这两种观点之外还有其他更为合理的理解?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其答案不仅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更将对今后的商标保护实践以及商标注册人的维权行动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鉴此,笔者不揣冒昧,特将自己在代理“头包西灵”商标案再审程序过程中,通过深入研读巴黎公约的规则架构及其内部逻辑关系所感悟到的对于如何理解其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涵义的一些拙见,成文于此,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二、案例简介
2002年5月28日,重庆市农业局批准重庆正通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通公司)生产销售通用名称为“注射用复方青霉素钾(I型)”、商品名称为“头孢西林粉针”的兽药产品。在正通公司递交给批准机关的申请表所附的标签式样中,商品名称“头孢西林”使用了特殊字体和字号并处于标签中的显著位置。
2002年7月27日,正通公司与四川华蜀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蜀公司)签订了《关于专销“头孢西林”产品的协议书》(以下称《专销协议》),协议约定:正通公司将“头孢西林粉针”产品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区域内专销,正通公司不得销售该产品,华蜀公司不得生产该产品;包装由华蜀公司设计,正通公司印制,包装上使用华蜀公司的“华蜀”商标,以华蜀公司合作开发、正通公司生产的形式印制,由正通公司组织生产产品;华蜀公司负责专销片区宣传策划,产品定价,承担销售费、宣传费、运输费等全部费用;协议期满或提前结束协议,正通公司继续生产销售该产品,取消华蜀公司的专销权,但不得继续使用“华蜀”商标等。
在双方合作期间,华蜀公司未经正通公司授权或同意,于2002年9月12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了与该产品专用商品名称相近似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并于2004年2月7日获准注册,注册号为第3304260号,核定使用在第5类兽医用药等项目上。
2004年1月7日,双方终止合作。此后正通公司继续使用上述专用商品名进行生产销售。
2004年2月24日,华蜀公司起诉正通公司使用的专用商品名“头孢西林”侵犯其注册的第3304260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权。此时正通公司方知华蜀公司的上述抢注行为,遂于2004年4月1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提出撤销“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申请。
2005年3月4日,商评委针对本案作出了撤销华蜀公司第3304260号注册商标的〔2005〕第289号裁定。在该裁定中,商评委指出,“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为自己产品拟定并经相关管理部门审批的专用商品名称,在双方签订《专销协议》前正通公司即已拥有了该专用商品名称权利。在实际使用的商品标签上,“头孢西林”处于显著位置,是消费者据以识别商品来源的主要标志。因此,“头孢西林”是正通公司经批准的专用商品名称,客观上该名称起到了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应视为正通公司的未注册商标。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签订的《转销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已明确,华蜀公司是正通公司“头孢西林”产品经销商,正通公司授权华蜀公司在全国专销。协议中还明确,合作结束后正通公司继续生产销售该产品,取消华蜀公司的专销权。因此,双方形成的是销售代理关系,在双方存在代理关系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华蜀公司未经被代理人正通公司授权,将与正通公司未注册的“头孢西林”商标相近似的“头包西灵Toubaoxilin”标识进行商标注册,足以使消费者混淆误认,其行为已构成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人未经授权注册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商评委做出了撤销华蜀公司第3304260号注册商标的裁定。
华蜀公司不服该裁定,在法定期限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2005)第289号裁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于2005年12月8日作出维持上述裁定的一审判决。
华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高院。2006年4月3日,北京高院对本案作出(2006)高行终字第93号终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原判以及商评委的(2005)第289号裁定。由于该终审判决没有责令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定,故其实质上维持了华蜀公司的第3304260号注册商标继续有效。本案二审的一个主要争议焦点为,正通公司与华蜀公司在合作期间是否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法律关系。针对上述焦点问题,二审判决首先将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代理关系解释为“该条款中的代理人即为商标代理人,即指接受商标注册申请人或者商标注册人的委托,在委托授权范围内,代理其委托人办理商标注册申请、请求查处侵权案件或者办理其他商标事宜的人。”在此基础上,二审判决推翻了一审判决以及商评委第289号裁定关于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之间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关系的认定结论,转而认定“本案华蜀公司与正通公司基于《专销协议书》而形成的是生产销售合作关系,一审认定二者形成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显系错误。华蜀公司通过自己使用‘头孢西林’商品名称,并使该商品名称商标化,其申请‘头包西灵Toubaoxilin’商标的行为不属于商标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基于上述理由及认定结论,二审判决撤销了一审判决和第289号裁定。
三、对商标法第十五条以及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代理人”涵义的法理解析
由于我国商标法第十五条在立法上完全是渊源于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二者中的“代理人”应属同一概念,具有相同涵义,因此,正确理解我国商标法第十五条的关键,在于对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涵义进行追本溯源,求索其立法本意。
在对巴黎公约的整个规则体系及其内在的逻辑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后,笔者认为,尽管巴黎公约没有对“代理人”的涵义作出专门规定,但根据巴黎公约规则体系中所蕴含的逻辑规律,完全可以对其中所使用的“代理人”这个概念推导出一个符合巴黎公约立法本意的准确涵义。应当指出,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规定的“代理人”,与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所规定的代理人,并不是一个涵义相同的法律概念,因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代理制度的规定去阐释巴黎公约中的“代理人”的涵义并将这个法律概念的本义限定为商标代理人的做法,已完全脱离了巴黎公约的整体逻辑,必然导致对巴黎公约相关规定的曲解和误读,并将降低乃至贬损巴黎公约整个规则体系的科学性和严谨度。
笔者认为,巴黎公约中所规定的“代理人”,其本义恰恰是指基于商事业务往来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而不是指商标代理人。唯有如此理解,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才能反映巴黎公约整个规则体系的科学性和严谨度,相反,如果将其本义曲解为商标代理人,则会凸显出巴黎公约这篇具有上百年历史并历经各国法律精英多次修改锤炼而成的光辉法律文献的立法漏洞和缺陷。
(一)巴黎公约作为一部保护工业产权的重要法律文献,既确立了对商标权的保护制度,也确立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制度,而无论是商标权还是专利权在权利获得方面都涉及代理问题,商标领域有商标代理人,专利领域也有专利代理人。但是,巴黎公约却仅在商标部分规定代理人未经授权不得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被代理人的商标,但在专利部分却并无类似的规定。这个失衡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不合理的立法疏漏,但其实际上恰恰是打开巴黎公约中“代理人”涵义的奥妙之门的一把重要钥匙。
如果我们把这里所使用的“代理人”这个概念的涵义解释为商标代理人,进而把这一条款解释为商标代理人在接受被代理人的委托进行商标注册时,未经授权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进行注册,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巴黎公约仅对商标代理人作出这种禁止性规定,而对专利代理人却网开一面,没有作出类似的禁止性规定。因为在专利代理领域同样存在着代理人违反代理合同的约定将被代理人的专利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的法律风险,而且这种做法同样应当是被禁止的。但是,为什么巴黎公约对专利代理中同样可能出现的这种违反代理约定的做法没有作出类似于商标部分的禁止性规定呢?我们无法为这种立法失衡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难道这是巴黎公约的一个“立法漏洞”?那么巴黎公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历经修改却又为什么始终没有填补这个“立法漏洞”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代理人”概念的涵义解释为基于商事往来关系而可以知悉被代理人商标的经销商,则上述疑问马上迎刃而解,而且上述所谓的“立法漏洞”不仅不属于真正的立法漏洞,反而恰恰反映了巴黎公约在规则构建上具有高超的科学性和严谨度,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则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所规制的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现象主要存在于商标领域,专利领域则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现象。
在商标领域中,商标所有人将其产品交付给具有商业合作关系的经销商后,经销商即可知悉标注在该商品上的被代理人的商标,只要该商标在经销商所在国家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尚未注册,则经销商就有可能以自己的名义将被代理人的商标在这些国家申请注册。这种做法在商业贸易实践中时有发生,且明显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商业道德,损害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但被代理人依据一般的商事法律又很难针对这种做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为此,巴黎公约才通过专项规定要求各成员国从商标法的角度提供适当的救济措施来制止这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商标抢注行为,因此,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实际上就是专门针对商标领域中特有的而一般商事法律制度又难以规制的经销商抢注被代理人商标的现象作出的。
而在专利领域中,上述现象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专利的申请需要符合新颖性和创造性要求才有可能获得授权,当专利技术方案的所有人将使用该技术制造的产品售出后,代理销售该产品的经销商一般很难通过产品本身知悉其制造技术,即使通过产品本身可以直接获知其中的技术方案,且该技术方案在经销商所在国尚未申请专利,则经销商实际上也已不可能再在其所在国以自己的名义将其所获知的技术方案申请并获得专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技术方案已因公开使用丧失新颖性而不符合专利授权条件。所以,在专利领域中,经销商通过正常的商事业务往来而知悉被代理人的产品制造技术并以自己的名义将其申请为专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经销商若能通过复杂的反向工程推导出产品中包含的技术秘密并将其申请为自己的专利,则这种行为也是完全合法的,不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巴黎公约才没有必要在专利部分作出类似于第六条之七的规定。
综上所述,如果将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理解为商标代理人的话,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巴黎公约为什么没有在存在同样代理问题的专利部分作出类似的规定,这个疏失就会成为巴黎公约的一个立法漏洞;相反,如果将其理解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商业合作关系的产品经销商的话,则第六条之七所要规制的抢注现象主要存在于商标领域,在专利领域不太可能发生,因此巴黎公约没有在其专利部分作出类似于第六条之七的规定就不仅不是立法漏洞,而恰恰体现了其规则体系的科学性和严谨度。
(二)如果将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理解为商标代理人的话,则该条款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就属于重复多余,而且其同各成员国原有法律体系中已存在的救济措施相比是一种变劣的救济措施;相反,如果将“代理人”理解为经销商,则该条款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在各成员国原有法律体系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巴黎公约创设该条款才具有积极意义,才会构成对各成员国原有法律体系的有益的补充,而不会成为多余而且变劣的救济措施并丧失其合理性和科学性。
如果将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的“代理人”理解为商标代理人的话,则该条款所规制的就只能是商标代理人在接受被代理人委托进行商标注册过程中违反约定擅自以自己名义注册被代理人的商标这种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显然存在着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代理人的上述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违约行为。针对这种违约行为,巴黎公约各成员国原有法律体系的民事代理制度和合同制度显然已经为此提供足够的救济措施,在发生上述违约注册行为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被代理人也完全可以依据相关的民事代理制度和合同制度而对代理人提出违约之诉,并可以要求司法部门责令代理人将其违约注册的商标归还自己。如此一来,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岂不成了一种画蛇添足的多余之举和一种不必要的立法重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公约所提供的救济措施相比于各成员国原有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救济措施而言,还是一种变劣的救济措施。基于已有的救济措施,商标的所有人可以要求代理人将其违约注册的商标直接归还自己,而巴黎公约所提供的救济措施为“该所有人有权反对所申请的注册或要求取消该注册,或者,如该国法律允许,该所有人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给自己。”可见巴黎公约本身并不直接提供归还商标的救济(这种救济需要从成员国的其他国内法律制度中寻找依据),只能提供“反对或取消注册”的救济。相对于归还的救济措施而言,巴黎公约所提供的显然属于一种变劣的救济措施,因为对于这种违约注册行为来说,仅仅“反对或取消注册”并不能构成对代理人之违约行为的有效惩处以及对被代理人所受损害的有效和充分救济,因为被代理人一般都是有偿委托代理人进行商标注册的,在代理人违反合同约定将商标注册为己有的情况下,如果相应的法律救济仅仅是该注册被反对或取消,那么对于被代理人所付出的代理费又如何处理呢?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显然没有对此提供救济,被代理人还需要另行通过合同违约之诉的救济措施索回!而且,根据巴黎公约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在“反对或取消注册”后,被代理人为了实现自己原来的注册目标还需要继续有偿委托其他代理人重新进行注册。凡此种种不便,使得商标所有人在其注册代理人违反委托代理合同擅自将被代理人的商标以自己名义进行注册的情况下,显然会优先选择民事代理制度和合同制度所提供的具有更好效果的救济手段。因此,对于商标注册过程中发生的代理人抢注被代理人商标现象来说,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所提供的是比已有救济手段效果更差的一种救济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岂不成了多余的、不必要的立法败笔?其科学性和严谨度还何以体现呢?
但是,如果将该条款中的“代理人”理解为商业合作关系中的经销商,则其所提供的救济手段就恰恰是各成员国的已有法律体系所欠缺和不能提供的,而且是规制经销商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注商业合作伙伴的商标的有效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的规定就是必不可少而且无可替代的。即便在今天的商业实践中,许多产品制造商与其经销商之间,仍然缺乏规范双方商业合作关系的合同,即使订有书面的产品买卖合同的,其中也很少会约定经销商未经授权不得抢注产品制造商的商标,因此,一旦发生上述抢注情形,则商标所有人往往很难依据合同制度获得有效的救济,加上双方的商业合作关系又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事代理,所以也不可能依据民事代理制度获得相应救济。由此可以想象,在巴黎公约签订时期的商业实践中,经销商抢注其商业合作伙伴商标而且得不到有效制止的现象也是经常发生的。为了维护诚实信用的商业道德和交易秩序,显然需要采取法律措施制止这种做法,但当时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体系并不能对此提供有效的救济,因此,巴黎公约为了弥补各成员国国内立法的欠缺并有效地规制这种违反诚实信用的商标注册行为,才专门在商标部分作出这种规定。
此外,这种理解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合理解释为什么巴黎公约没有在专利部分作出类似于第六条之七的规定。正因为商标注册代理过程中发生的代理人抢注被代理人商标的行为可以通过民事代理制度和合同制度中的救济手段予以规制,所以第六条之七的规定实质上是专门针对商业贸易往来中经销商抢注被代理人商标的现象而作出的,同样,专利申请代理过程中发生的代理人将被代理人的专利据为己有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民事代理和合同制度中的救济手段予以规制,而专利领域实际上也不存在象商标领域那样的经销商擅自将被代理人的专利据为己有的情形,因此,巴黎公约才没有而且也不需要在专利部分作出类似于第六条之七的规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结合巴黎公约的整个规则体系及其内在逻辑关系来理解第六条之七的规定,才能科学、准确地把握其真正的立法意图及真实涵义,而不会望文生义、误入歧途,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只有把第六条之七中规定的“代理人”解释为经销商,才能对巴黎公约中的整体规则安排作出合理解释,才能使巴黎公约的科学性和严谨度得到完整体现,因此,这个解释才是符合这项规则的立法本意的科学解释。
结合上述对巴黎公约第六条之七中“代理人”涵义的法理解析,再来审视商标行政执法部门在《商标审理标准》对同一个概念的扩大解释以及北京高院在“头包西灵”诉讼案中对此所作的判例解释,笔者认为,司法部门将上述“代理人”的涵义限定为商标代理人,将经销商排除在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这种理解与巴黎公约设立该条款的立法本意无疑是南辕北辙的,而商标行政执法部门虽然已将经销商纳入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但却把这种观点作为一种延伸的扩大解释,并仍然认为巴黎公约中“代理人”的本义是指商标代理人,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解。相反,笔者认为,把该条款适用到商标代理人身上的做法,才恰恰是对巴黎公约关于“代理人”的原本涵义的一种延伸和扩大解释。
- 戻る: 『特許権侵害訴訟にはいかに「余...
- 次へ: 「薬品特許権侵害の司法救済と抗...
- 復帰